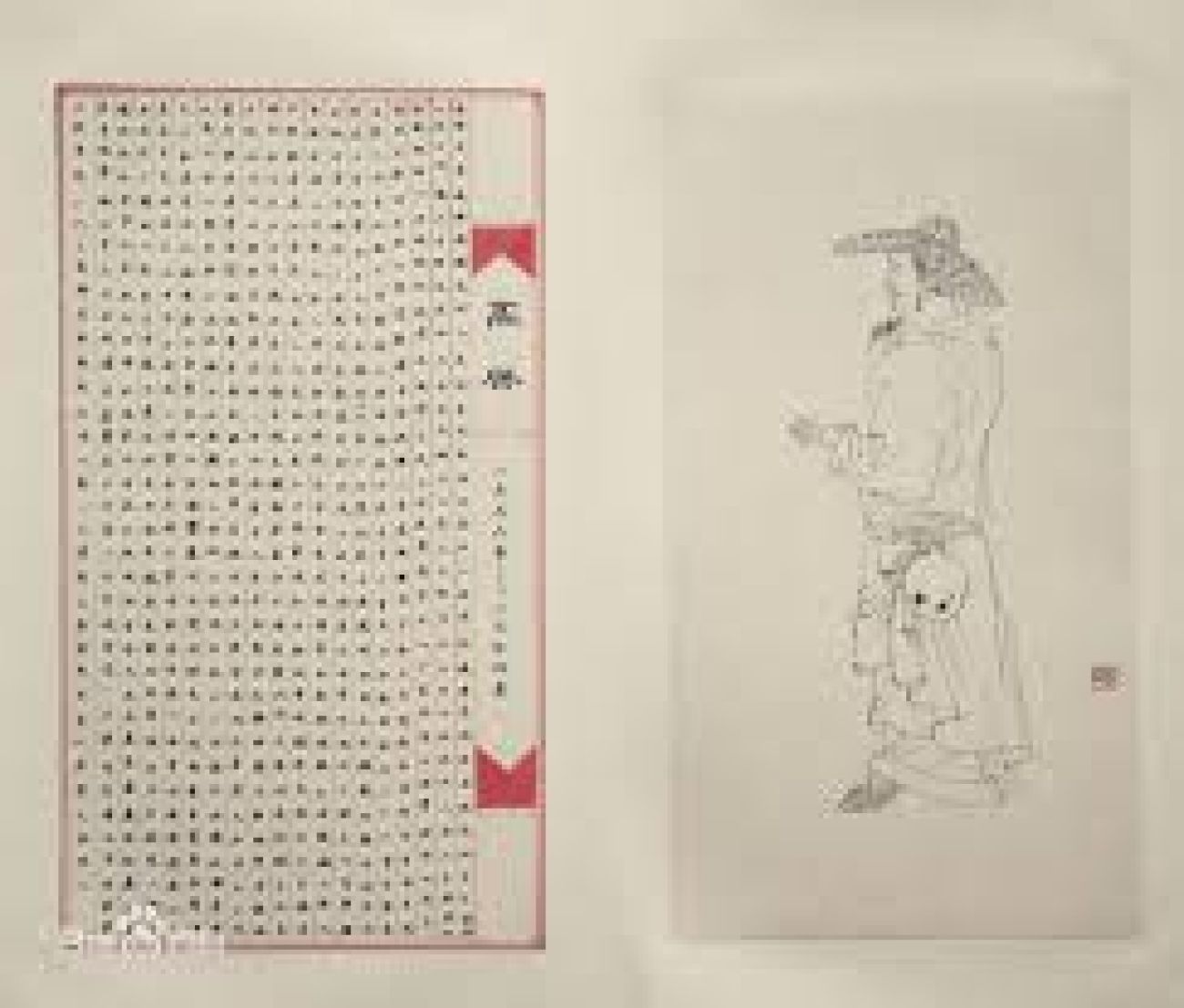
青丘詩魂 之 龍蟠虎踞四字誅心
白骨為碑血為墨,山川誰記舊詩人。若教筆下無悲意,天下應無讀書人。
洪武十三年(1380),南京城風聲鶴唳。朱元璋誅藍玉、胡惟庸,整肅百官,文人之筆成了最危險的刀。就在這一年,蘇州詩人高啓因一篇《上樑文》,被指「語涉不敬」,腰斬於市,寸裂八段。他的罪名不在謀反,不在失職,僅僅在「龍蟠虎踞」四字。
四字之禍,成為明初最詩意、也最殘酷的死亡。
關於高啓為何被朱元璋處以「腰斬」之刑,歷代史書雖記載簡略,但可以根據《明史》《太祖實錄》及明清文人筆記,整理出最可信的幾個層面來看:
《明史·文苑傳》載:「高啓性疏放,好飲酒。嘗醉書詩,語涉不敬,太祖怒,下獄,命腰斬。」這是唯一被官方正史所記的直接原因:「醉書詩,語涉不敬」。也就是說,他在酒後寫詩,詩句中有冒犯皇帝、諷刺朝政的語句。
可惜那首詩的原文早已不存。歷代筆記中出現過三種傳說版本,雖無定論,但可窺見大致方向。傳聞詩中有一句:「白日青天亦可疑。」這句話被後世多次引用,意指朱元璋猜忌多端,連青天白日都不可信。若真有此句,確實極具諷刺意味,對開國皇帝而言無異「以筆弒君」。這一說最為流行,但無原詩可證。
《明史紀事本末》與清人筆記《今獻備遺》皆提到,高啓在《禁酒詩》中怨言過多。
朱元璋頒禁酒令時,高啓仍嗜酒成性,私下作詩調侃法令。傳言詩中有句:「朝禁杯中物,臣醉不須君。」
此詩意若真存在,等於公然宣稱「我醉不為君醒」,即以文人之傲反抗帝制權威。這句若為真,確實可致殺身之禍。
明太祖屢誅開國功臣,如藍玉案、胡惟庸案等,高啓與文士相聚時曾作詩憫之,傳有句:「兔死狗烹,英魂不返,空餘白骨照中原。」此乃用典之語,暗指「兔死狗烹」之事,影射皇帝恩將仇報,若此句為真,觸忤龍顏更甚前兩說。
清人王昶《桐陰論詩》曰:「高青丘以詩死,非誣也。洪武之世,天子以筆為刃。青丘不慎,言涉忤上。」
近代學者陳寅恪認為:「所謂醉詩,不過藉口。太祖惡其傲氣耳。」意即:高啓之死,或非一詩之禍,而是積怨所致。的確,高啓性情放達、言語直率,對太祖雖敬而不懼。
他在翰林修《元史》時,屢以文字「不奉詔意」而被警告。
朱元璋性情多疑,見其詩氣過高,恐其不臣,遂借酒詩為名,行誅滅之實。
綜合史料與文人記載,最可信的結論是:酒後作詩語涉不敬(或諷君、或戲政、或犯禁),性情高傲、恃才不恭、與權力格格不入。換言之,他是死於性格與氣節。詩只是引線。
朱元璋對文士極忌「自尊不臣」,而高啓恰是此類人。
太祖曾言:「朕最惡書生放言無忌。」
於是,一首詩,便足以送一代詩人入刑。
龍蟠虎踞四字誅心「筆端生風,言出招禍;一紙上樑文,竟換得血染青丘。」——《吳中野錄》題記。「龍蟠虎踞」一語出自《三國志》:「此地形勝,真龍蟠虎踞之勢。」原指建業(今南京)地勢雄偉。
然而,到了元末亂世,張士誠據蘇州,自稱「龍盤虎踞之都」。這四字遂被政治化,成為「舊吳國」的象徵。
高啓出身蘇州,少時為張士誠幕客。張氏敗後,朱元璋雖釋其罪,仍對這批「故張之臣」心存猜忌。當他為友人建宅撰《上樑文》,用「龍蟠虎踞」形容屋勢,本是尋常修辭,卻被告者解讀為「懷念舊主,頌賊之都」。
朱元璋聞報大怒,曰:「此子心在張氏,筆為奸語!」命捕入獄。
洪武之世,最可怕的不是「造反」,而是「思想不純」。
朱元璋出身貧賤,極懼士人「藉筆議政」。
他曾言:「朕最惡書生,口似蜜而腹如刀。」
高啓性放達,酒後好言直語。
修《元史》時屢以「不奉詔意」受責;又與文人群聚飲詩,時有譏諷朝政之辭。
「龍蟠虎踞」不過是最後一根稻草。
朱元璋早對他心存戒懼,只待一語借口。
「太祖命磔其身為八段,以示後學。」
此刑象徵「分裂不臣之魂」,一如方孝孺後被「誅十族」,皆是以極刑警告天下文人:「筆不為朕,便為逆。」
有人說,朱元璋在宮中讀到《上樑文》原稿時,冷笑道:「龍蟠虎踞,本朕之都,汝何以頌之?」
史家多以為:「上樑文」之說,或為後人對「醉書詩語涉不敬」的具象化。
然而,考其情理,卻極為合理:高啓確曾為張士誠幕僚;「龍蟠虎踞」確為蘇州舊號;洪武年間文字獄頻仍;高啓被腰斬之酷刑,亦顯非常罪。
因此,雖無原稿存世,但作為「以文誅心」的歷史象徵,這說法可信其意,不可信其字。
朱元璋恐文人不臣,高啓信詩人有道。一個以權築城,一個以詩為國。他們皆出身寒微,皆志在天下,卻終因距離太近,而必有一人要死。
洪武之世的血腥,並非因皇帝嗜殺,而是因他懼怕那種「筆能動人心」的力量。
高啓死後,朱元璋據說歎道:「此人有才,恨不為朕用耳。」
這一句,成了文人命運的訃詞。
「龍蟠虎踞」四字,原本是讚美山川之勢。然而,當權力將語言視為武器,文字便不再無辜。
高啓之死,不是因四字,也非因酒詩,而是因他相信詩人的筆能高於君王的劍。他以詩築心,而帝以刑毀之。終於,詩勝了。因為數百年後,世人忘了那座宮闕的名字,卻仍記得那個被腰斬的詩人高啓。
明清以後,文人視高啓之死為「以詩殉道」的象徵。
清人冒襄有詩曰:「青丘一笑成千古,筆底風雲不肯休。」
王士禎評曰:「詩之死於明,始於高青丘。」

